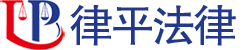防衛型刑事案件辯護心得
發布時間:2019-01-22 瀏覽次數:383 來自: 律平法律服務成都有限公司
防衛型刑事案件辯護心得
一
正當防衛的刑法規定
《刑法》第二十條 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
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 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01
一般正當防衛
一般正當防衛(第1款):是針對正在進行的一般不法侵害行為所進行的防衛。具有防衛限度的限制,存在防衛過當的問題。
02
防衛過當
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怎么理解這句話?因為它的前提是“正當防衛”超過限度,也就是說前提是你的內心或者你的行為所表現出來的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是有符合正當防衛的這么一種基本條件的,只不過是因為你超出了限度,突破了正當防衛合法“免責”的本性了。
03
特殊正當防衛
20條第3款是對特殊防衛的規定。是針對于行兇、殺人、搶劫、強 奸、綁架這樣的一些惡性案件。這些犯罪情形危及的都是人身。它的范圍非常窄,針對這種情況的暴力犯罪,采取的防衛行為沒有限度限制。簡而言之,這是一種有條件的無限防衛。對防衛范圍有所限制而無強度限制。
“
我們做律師的實際上第二種情形遇到的是多的,因為在很多的暴力犯罪過程中,往往“受一 定侵害”的被告人在實施反擊行為的時候就容易過了。經常會發現被告的律師在辯護的時候往往都有這么一條:“我們這個行為是防衛行為,雖然我把他砍了或者我把他怎么樣了,但是我的行為是在他有過錯的情況下,對我的人身有威脅的情況下,我實施的這個行為。”所以說,這種情況是比較多的。
”
二
高檢相關指導性案例分析
案例一:陳某正當防衛案
未成年學生,尾隨、攔截陳某(未成年學生),質問其向老師告發他們打架之事,陳解釋沒有告狀,9人等遂圍毆陳某。其中,有人用膝蓋頂擊陳某胸口、有人持石塊擊打陳某手臂、有人持鋼管擊打陳某背部,其他人對陳某或勒脖子或拳打腳踢。陳某掏出隨身攜帶的折疊式水果刀(不屬于管制 刀具),亂揮亂刺,刺中其中3人,均構成重傷二級。
陳某逃脫。部分圍毆人員繼續追打并從后投擲石塊,擊中陳某背部和腿部。陳某經人身檢查,多處軟組織損傷。
裁判要旨在被人毆 打、人身權利受到不法侵害的情況下,防衛行為雖然造成了重大損害的客觀后果,但是防衛措施并未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依法不負刑事責任。
首先,要確定行為性質。行為人面臨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反擊行為具有防衛性質。
其次,分析工具和主觀意識。這個工具是他隨身攜帶的,別人不打他,他也是帶著這個小刀的,這里肯定不是準備這個工具傷害某個人,甚至不能評價他是用來自衛的。再一個,就是主觀意識。他不可能主動挑釁九個人,所以他主觀肯定是躲避的。
那么關鍵的問題或者說是不容易判斷的是什么呢?這個措施有沒有超過必要限度,有沒有造成故意、重大的損害。一個重傷就是重大損害,三個自不在話下。但是法院認為,這九個人用比較嚴重的這種手段、措施去傷害這一個孩子,防衛結果雖客觀上造成重大損害,但防衛措施并未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不能認定為防衛過當。
這個案子的后檢查院后沒有批捕,終也就不再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案例二:朱鳳山故意傷害(防衛過當)案
朱鳳山之女朱某與丈夫齊某鬧離婚,回娘家住。齊某不同意離婚,經常到朱家吵鬧。吵鬧過程中,將朱家門窗玻璃和汽車玻璃砸壞。朱為防止齊某再進入院子,將院子一側的小門鎖上并焊上鐵窗。
某日22時許,齊某酒后駕車到朱家,欲進院子未得逞,在門外叫罵。朱女不在家中,僅朱鳳山夫婦帶外孫女在家。朱鳳山將情況告知齊某,齊某不作罷。朱鳳山又分別給鄰居和齊某的哥哥打電話,請他們將齊某勸離。經鄰居勸說,齊某駕車離開。
23時許,齊某駕車返回,搖晃、攀爬大門,欲強行進入,朱鳳山持鐵叉阻攔后報警。齊某爬上院墻,用瓦片砸朱鳳山。朱鳳山躲到一邊,并從屋內拿出宰羊刀防備。
隨后齊某跳入院內徒手與朱鳳山撕扯,朱鳳山刺中齊某胸部一刀。朱鳳山見齊某受傷把大門打開,民警隨后到達。齊某因主動脈、右心房及肺臟被刺破致急性大失血死亡。
裁判要旨
在民間矛盾激化過程中,對正在進行的非法侵入住宅、輕微人身侵害行為,可以進行正當防衛,但防衛行為的強度不具有必要性并致不法侵害人重傷、死亡的,屬于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應當負刑事責任。
本案關鍵就在于拿刀的這個行為,以及捅傷的這個結果,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法律能夠保護。
這個案子一開始判“沒有防衛性質”,一審的時候判朱鳳山純粹就是故意傷害。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判了15年。然后被告上訴,二審法院認為“齊某雖實施了投擲瓦片、撕扯的行為,但整體仍在鬧事的范圍內,對朱鳳山人身權利的侵犯尚屬輕微,沒有危及朱鳳山及其家人的健康或生命的明顯危險。”認可了行為具有防衛性質,但防衛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屬于防衛過當。而且很明顯就是想要傷害。所以定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改判了,判了7年。
案例三:于海明正當防衛案
某日9時許,于海明騎自行車正常行駛,劉某醉酒駕小轎車向右強行闖入非機動車道,險些碰擦。劉某一名同車人員下車與于爭執,經同行人員勸解返回時,劉某突然下車,上前推搡、踢打于海明。雖經勸解,劉某仍持續追打,并從轎車內取出一把砍 刀(系管制 刀具),連續用刀面擊打于海明頸部、腰部、腿部。
劉某在擊打過程中將砍 刀甩脫,于海明搶到砍 刀,劉某上前爭奪,在爭奪中于海明捅刺劉某的腹部、臀部,砍擊其右胸、左肩、左肘。劉某受傷后跑向轎車,于海明繼續追砍2刀均未砍中,其中1刀砍中轎車。
劉某逃離后,因腹部大靜脈等破裂致失血性休克于當日死亡。
裁判要旨
對于犯罪故意的具體內容雖不確定,但足以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行為,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的“行兇”。行兇已經造成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緊迫危險,即使沒有發生嚴重的實害后果,也不影響正當防衛的成立。
“
昆山龍哥案被作為指導性案例,一個重要的價值就是在于對“行兇”做了比較細致的陳述。在20條第3款里頭,講到了“行兇”。但是我看了一些法學家寫的教材,對于“行兇”的描述不像這個案例寫的這么生動。
”
這個案子里頭講到了三個要點。
01
劉某的行為是否屬于行兇否定說不是行兇。因為他在打于海明的時候是用刀面拍的,可能他是想要震懾或者是想要用輕微的方式來毆 打于海明,犯罪故意的具體內容不確定,不宜認定為行兇。肯定說對行兇的認定,應遵循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以“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作為把握的標準。你手里拿著刀,誰知道你是故意拍我,還是你喝醉了酒你手上沒準。如果你手腕稍微換一個90度的角度的話,那就是“劈”了。
高檢觀點
高檢認為對于犯罪故意的具體內容雖不確定,但足以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行為,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的“行兇”。
02
劉某的侵害是否屬于正在進行?
于海明搶到砍 刀,那個人刀離手了,再去捅他,合理嗎?
否定說
于海明搶到砍 刀后,劉某的侵害行為已經結束,不屬于正在進行。
肯定說
判斷侵害行為是否已經結束,應看侵害人是否已經實質性脫離現場以及是否還有繼續攻擊或再次發動攻擊的可能。
高檢觀點
高檢支持肯定的意見,在于海明搶得砍 刀順勢反擊時,劉某既未放棄攻擊行為也未實質性脫離現場,不能認為侵害行為已經停止。
03
于海明的行為是否屬于正當防衛?
否定說
于海明本人所受損傷較小,但防衛行為卻造成了劉某死亡的后果,二者對比不相適應,屬于防衛過當。
肯定說
不法侵害行為既包括實害行為也包括危險行為,對于危險行為同樣可以實施正當防衛。
高檢觀點
要求防衛人應等到暴力犯罪造成一 定的傷害后果才能實施防衛,這不符合及時制止犯罪、讓犯罪不能得逞的防衛需要,也不適當地縮小了正當防衛的依法成立范圍。
三
曾辦案件介紹分析
“
“龍哥案”出現之后,我就回過頭反思我自己過去做的案子。就是馮某甲的案子,我們團隊認為構成無限防衛。
這個事情我認為可以拿出來作為一個教材,它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無限防衛。
”
案情概況
當事人是一個屠夫。2016年春節之后1月5號(指的是臘月初五)9點鐘時候聽到有人敲門,他開門看到戴帽子的黑衣人。這個人進來就砍他,他就用左手抬起來護頭,后退過程中,胳膊又挨了一刀,身體上又挨了一鞭子,于是他就退到院子里頭,院子里頭有小窗、小窗上有鐵剪子和鐵刀、剔骨刀。然后就到了大門外,到了大門外一米五處,這個人用長的鐵鞭子又打他的頭。他戴了毛線帽,在被打過程中這個毛線帽就掉下來了,把眼睛擋住了。他拿刀子的手不自覺的就在身前亂揮,后來癱倒在地上,等了一會兒才起身,看到一個人搖晃著往北走,走了十幾步已經就趴在地上。他就起來走過去一看,那個人身上有血,他就害怕了,打120、打110,然后警察來了,被害人經搶救無效死亡。
公安立案是按照“故意傷害”立的,對于他的強制措施,是監視居住,也就是沒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公安機關的起訴意見書也是定性成“故意傷害”。
辯護思路分析
“
關于事實的陳述,律師不要在案卷之外去做任何的添油加醋。因為律師如果說是講這些不客觀的東西的話,表明職業性有所欠缺。 所以說我讓當事人自己寫案發過程,然后我援引上來。
”
01
分析死者的行為
對于死者趙芳國行為的分析,概括的說是故意殺人,并且屬于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事件。下面事實和情節加以證明:一是趙芳國作案時實施的行為是明顯的、典型的故意殺人行為。寒冬黑夜、頭戴長蛇帽、面戴口罩,進門也不說話,見人就朝頭砍等等。在他的車內發現6個燃燒 瓶、爆炸 物、打火機等物品,尤其是爆炸 物品隨手可及,足以說明他做好了放火、爆炸、殺人、傷害的充分準備。其作案時對自己的面部進行了掩蓋,使人難以辨認,車輛未上鎖、鑰匙在車上隨時可逃離,車輛號牌進行了偽裝、逃離打擊,說明對本案做了充分的準備。這一段是我們分析死者的行為,死者行為的這種惡劣程度也表現出來,起碼讓人知道死者來者不善。
02
被告人行為的過程和法律性質的分析
根據現場血跡,經鑒定是被告所留,而且是僅有的血跡,只能說明被告人從院子里往外走的過程中被砍破左手滴落的,這個事情就能明確了。不管是被告人將趙芳國趕出大門,還是趙芳國將被告人趕出,不管是怎么出去的門,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的手是在這個結骨眼上砍破的。
值得注意的是,被告人的陳述前后有所出入。這是因為,當事人說的話很可能是事后形成的一種思路,并不是當時狀況的一種陳述。在夜 色籠罩之下,在極其緊迫的生死關頭大刀已經砍在臉上、胳膊上的情況下,一般人都不太清晰記住當時一兩秒或者兩三秒情形,所以即使說法不一致也不存在撒謊,以上情況都有可能存在。但是這些東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當時的情況下會發生什么。
從窗上拿起刀向他舞扎到走出家門過程,被告人客觀上沒有傷害到趙芳國,主觀上沒有產生要傷害趙芳國的故意。但是到了腦袋被砸、眼睛被遮住之后,出于本能而不是積極的主觀意識,開始持刀亂捅。這個時候他即使意識到可能傷害到對方,但是他也只有這樣做。總之這是一種本能,從主觀上來說,當時可能確實意識到持刀揮舞可能會傷害到對方,甚至在極短的時間內感覺到自己已經捅上對方了,但是辯護人認為這仍然是為了保護自己采取的正當防衛。這就是行為的過程。這就是第三部分,就是說從法理上來講述這個問題。我認為這就構成了無限防衛。
律平法律服務成都有限公司
聯系方式:18502858003
詳細地址:成都市武侯區武侯大道雙楠段90號附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