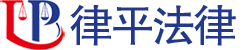確認合同糾紛違約方的賠償責任應當遵循可預見性原則
發布時間:2019-06-27 瀏覽次數:387 來自: 律平法律服務成都有限公司
確認合同糾紛違約方的賠償責任應當遵循可預見性原則
確認合同糾紛違約方的賠償責任應當遵循可預見性原則——新疆亞坤商貿有限公司與新疆精河縣康瑞棉花加工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1.裁判要旨
在審理合同糾紛案件中,確認違約方的賠償責任應當遵循“可預見性原則”,即違約方僅就其違約行為給對方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對由于市場風險等因素造成的、雙方當事人均不能預見的損失,因非違約方過錯所致,與違約行為之間亦沒有因果關系,違約方對此不承擔賠償責任。
1.基本案情
2004 年1 月2 日,亞坤公司與康瑞公司簽訂棉花購銷合同,約定康瑞公司向亞坤公司提供229 級(二級)皮棉1370 噸,單價每噸16 900 元,皮棉質量按國家棉花質量標準GB 1103 - 1999 執行,康瑞公司對質量、重量負責到底,質量、重量出現重大問題,以公證檢驗為準。后經鑒定顯示:康瑞公司向亞坤公司所供皮棉總計:二級皮棉1 . 618 噸;三級皮棉523 . 416 噸;四級皮棉564 . 525 噸;五級皮棉21 . 643 噸,合計重量為1111 . 202 噸,銷售貨款合計12733 990 . 29 元,亞坤公司貨款本金損失為6 659 358 . 11 元。《2004 年棉花市場回顧及2005 年市場展望》一文載明:由于2003 年棉花減產,國內棉花銷售價格一度沖至1 . 75 萬元/噸的水平。價格如此飆升,既有產需缺口擴大的因素的影響,也有“買漲不買跌”的恐慌心理在起作用。而在國家分兩次共增發150 萬噸配額和緊縮銀根等宏觀調控政策引導下,國內棉花價格出現了回落,棉花銷售價格在6 月下降到了1 . 5 萬元/噸,隨后受2004 年棉花大豐收心理預期影響,國內棉花價格跌速加快并沖破了數道心理防線。目前,國內棉花銷售價格已經下降到了1 . 13 萬元/噸,比年初下降了35%。
1.裁判觀點
一審法院認為:根據雙方簽訂的棉花購銷合同第4 條約定:供方對質量、重量負責到底,質量、重量出現問題,以公證檢驗為準。故此,康瑞公司對提供給亞坤公司的棉花,在其轉讓時仍應對質量、重量問題負責到底。在本案雙方合同的實際履行過程中,康瑞公司向亞坤公司交付的皮棉存在嚴重的質量和數量問題,導致亞坤公司與新疆博州棉紡織(集團)有限公司加工32支紗、40 支紗的委托加工合同不能履行,亞坤公司買賣合同的目的不能實現,康瑞公司的行為構成根本違約,故亞坤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訴訟請求符合法律規定和雙方當事人的約定,法院予以支持。
在亞坤公司提取此棉花后,棉花市場價格發生重大變化,棉花價格開始逐月下滑。為防止該批棉花發生因價格下滑造成的損失,截至2005 年2 月7 日,亞坤公司已將康瑞公司交付的棉花全部出售,相互返還已不可能。針對棉花市場價格波動,雖經采取措施補救,但仍造成亞坤公司一 定資金的損失。對亞坤公司因此所蒙受的貨款本金損失,康瑞公司理應承擔主要賠償責任。亞坤公司在棉花價格顯著下滑情況下,未及時采取措施,怠于出售,失去棉花銷售佳時機,對造成該批棉花本金損失也有一 定過錯,亞坤公司亦應承擔相應的責任。
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合同簽訂的2004年1月,恰逢國內棉花市場價格飛漲,但到了2004 年5、6 月以后,棉花市場價格回落,此期間每噸相差5000 ~ 6000 元。亞坤公司在2004 年6 月以后轉售的棉花,即使質量等級不變,也必然會出現因市場行情所致的收益損失。原審判決認定的亞坤公司本金損失6 659 358 . 11元不僅包括了棉花減等的差價損失,亦包括在此期間因市場行情下跌所造成的收益損失。該部分收益損失顯屬市場風險造成的,非為雙方當事人所能預見,亦非康瑞公司過錯所致。
因康瑞公司與該部分損失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故康瑞公司不應承擔市場行情變化導致的亞坤公司的收益損失。原審判決將亞坤公司在市場行情低迷時基于轉售關系所形成的銷售價格與本案行情高漲時形成的購買價格之差作為亞坤公司的損失由雙方分擔顯屬不當,不僅合同關系各不相同,亦有違公平原則及過錯責任原則,二審法院予以糾正。亞坤公司關于康瑞公司應補償其棉花收益損失6 152 857 . 22 元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二審法院對亞坤公司在購買棉花時所發生的實際損失,即棉花重量虧噸損失及質量減等的差價損失予以確認,對于其他損失部分,即市場風險所致的收益損失、轉售期間發生的運輸費用、與案外人發生的借貸利息損失,均因缺乏合同依據及法律依據而不予支持。
代表性學術觀點
可得利益賠償問題的立法表達與司法實踐呈現脫節狀態,裁判者舍棄立法確立的作為賠償規則的可預見性規則的適用轉而訴諸立法沒有規定的確定性規則。為彌補立法與司法的上述區隔,學理上分別從可預見性規則的完善以及確定性規則的建構兩個方面作出如下努力:
吳行政認為(參見:吳行政:《合同法上可得利益賠償規則的反思與重構》,載《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第69~75頁),應結合可預見性規則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司法實踐對確定性規則的需求對可預見性規則予以完善并確立確定性規則。就可預見性規則的完善而言,主張:
第 一,區分“通常情形下”的預見與“特別情況下”的預見,對前者借鑒比較法上的立法例引入債權人信息披露義務,作為預見的認定基準。
第二,在適用可預見性規則時應排除故意或重大過失違約。
第三,可預見性規則的內容應明確規定為損害的類型而非程度。
就確定性規則的制度構建而言,主張:非違約方應當提供證據證明可得利益的存在及其數額,但人民法院根據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夠推定出可得利益存在的事實的,當事人無須舉證證明;對于可得利益數額,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予以裁量。對于可得利益存在的證明標準應根據可得利益本身的未來性、不確定性的特點予以降低,即采取較低蓋然性證明標準。對于可得利益的損失與違約行為之間因果關系和非違約方的過失產生的損失、非違約方沒有及時采取合理措施而導致的損失的擴大,以及非違約方因違約而獲得的利益的證明,則采用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
劉承韙針對題設問題,提出了違約可得利益損失的確定規則。(參見:劉承韙:《違約可得利益損失的確定規則》,載《法學研究》2013年第2期,第84~101頁。)程序性確定規則的建構以證明標準的降低為價值取向,從三個方面實現:
第 一,引入“合理確定性標準”,即以非違約方所舉示的證據能夠證實其可得利益主張具有“合理確定性”的基礎,以此取代可預見規則;
第二,建立“事實與數額區分”的證明標準,即當事人只需要證明損害的“事實”具有合理確定性即可,而無須證明損害的“數額(范圍或程度)”具有合理確定性;
第三,放寬自由心證與經驗法則的運用,即上述合理確定性標準中的“合理”及事實與數額區分標準中的“數額近似值”需要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證和經驗法則進行判斷,但應以非違約方能夠證明有可得利益損失的事實但沒有任何可直接參考的標準為適用前提。
實體確定性規則的建構以增強可操作性為價值取向,并以“營業”為中心,對可得利益計算標準進行類型化:
第 一,自身營業利潤標準,即以自己的營業利潤為標準來計算本次違約給非違約方造成的可得利益損失;
第二,他人營業利潤標準,即類推適用和參照執行同行營業利潤來計算非違約方的可得利益損失;
第三,新營業標準,即以“新營業規則”來計算新營業可得利益損失;
第四,替代性標準,即上述諸種營業標準難以奏效時,針對違約損害的特殊情境所采取的信賴利益標準、類推適用財產租賃價值或財產信息、機會損失等特殊的替代性標準來支持非違約方的可得利益損失。
基于同樣的問題意識,郝麗燕則從多角度論證了“可預見性”要件的必要性和主要內容,并從證明標準角度論證了“確定性規則”的不合理性,取而代之以“極有可能性”的證明標準,即非違約方只要證明可得利益根據事物的一般發展規律“極有可能產生”已足,并就可得利益損失的計算提出了具體計算或抽象計算方法。(參見:郝麗燕:《違約可得利益損失賠償的確定標準》,載《環球法律評論》2016年第2期,第48~66頁。)
此外,學理上對解約與撤銷的可得利益賠償問題也進行了相關探討。(參見:參見王躍龍:《解約可得利益賠償之辨》,載《政治與法律》2006年第5期;尚連杰:《合同撤銷與履行利益賠償》,載《法商研究》2017年第5期
案號:高法院(2006)民二終字第111 號
案例來源:《高人民法院公報》2006年第11期
律平法律服務成都有限公司
聯系方式:18502858003
詳細地址:成都市武侯區武侯大道雙楠段90號附5號